秦蕙田《五禮通考》撰作特點析論
作者:楊志剛
來源:《經學研討集刊》第三期
中國現代禮學著作中,篇幅最長、內容最多者,當推江蘇金匱(今無錫)秦蕙田(字樹峰,號味經,1702—1764年)的《五禮通考》。以臺灣影印的《文淵閣四庫全書》而言,《五禮通考》占據了其經包養合約部第129冊至第136冊近8冊的容量,共計7317頁。若以每頁670字算,總字數在490萬字以上。[1]可資比較的是,同在這套影印的四庫全書中,同屬禮學著作中部頭年夜的如清初徐乾學《讀禮通考》,只要3冊、2349頁;宋代衛湜《禮記集說》為4冊、3217頁,清代《欽定禮記義疏》為3冊、2162頁。
《五禮通考》不僅卷帙眾多,且在禮學史上享有很高的聲譽。時彥評它為“數千百年來所絕無而僅有之書”[2],“懸諸日月不刊之書……獨冠古今”[3]。以后曾國藩贊其“舉全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年夜思精矣”,并將秦蕙田列為自古以來32位圣哲之一,重點推薦給后代[4]。《清史稿》卷三〇四為秦蕙田列傳,稱此書“廣博閎遠,條貫賅備”。經過多年的枯寂和淡然以后,古人從頭將眼光投向《五禮通考》。1994年,臺灣圣環圖書公司依據王欣夫傳授加入我的最愛的原刊初印樣本照片影印《五禮通考》(以下簡稱圣sd包養環本),并在“出書說明”中強調:這部“禮學杰作”,對于清楚我國現代禮制沿革,“實為最切實用之書”。近年來,已有兩篇專題論文問世,介紹和探討其人其書。研討者指出,此“可謂中國現代禮學集年夜成著作”[5],或以為“成書尤非易事,其成績亦斐然可觀”[6]。

【圖為秦蕙田《五禮通考》書影】
本文重要關注《五禮通考》的撰作特點,并將考核的視角集中在:(一)現代禮學的演變尤其是若干主要線索的梳理,借此對《五禮通考》在禮學史上的意義和位置有所闡明。(二)秦蕙田的生平經歷、文明佈景與其學術撰著之間的關系,由此深刻探析這般鴻篇巨制的成因和價值。在此基礎上,試圖進一個步驟歸納綜合《五禮通考》所體現的禮學著作形態上的新特點,剖析其意義及局限。
一
至多有4部後人的著作,給秦蕙田撰作《五禮通考》以主要的啟發和影響。
《儀禮經傳通解》
這是朱熹曾反復念叨并屢次設定人手編撰的“禮書”,初名《儀禮集傳集注》,暮年確定此名,并修葺親定此中的二十三卷。后由門生黃榦、楊復等續完。據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年甫逾包養合約冠的他即與同好配合研討“三禮”,并特別留心于“朱子當日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為本,編次朝廷公卿年夜夫士平易近之禮,盡取漢唐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證,以為當代之典”。可他又感歎:“今所觀《經傳通解》,繼以黃勉齋、楊信齋兩師長教師修述,究未足為完書,是以‘三禮’疑義至今猶蔀。”于是觸動了他參照《儀禮經傳通解》的方式往探討禮學,“乃于禮經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廟、禘嘗、饗宴、朝會、冠昏、賓祭、宮室、衣服、器用等,先之以經文之互見錯出足相印證者,繼之以注疏諸儒之牴觸訾議者,又益以唐宋以來專門名家之考論發明者,每一事一義,輒集百氏之說而諦審之。審之久,思之深,往往如進山得徑,榛蕪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猶未敢自負也。半月一會,問者、難者、辨者、答者,回旋反復,務期愜諸己,信諸人,而后乃筆之箋釋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余年,而裒然漸有成秩矣”[7]。顯然,對于秦蕙田走上研治禮學之路,并平生孜孜以會通、考辨的方式對禮學加以周全的清算,《儀禮經傳通解》起到了引領的感化。
《讀禮通考》
徐乾學(1631—1694年)的這部研討現代喪禮的高文,秦蕙田是在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1747—1748年)丁父憂還鄉治喪時讀到的。后出的《四庫全書總目》稱:“古今言喪禮者,蓋莫備于是焉。”該著的特點是“于《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及《鉅細戴記》,則仿朱子《經傳通解》,兼采眾說,分析其義。于歷代典制,則一本野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四庫全書總目·讀禮通考撮要》。撮要還指出:“乾學又欲并修吉、軍、賓、嘉四禮,方事排纂而歿。”(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68頁)。讀見此書,秦蕙田既興奮又深感缺甜心花園乏,以為它“規模義例俱得朱子本意,唯吉、嘉、賓、軍四禮尚屬闕如”,遂啟動了《五禮通考》的撰作。他“陳舊篋,置抄胥,發凡起例,一依徐氏之本,并取向所考定者,分類排輯,補所未及”[8]。盧文弨(1717—1795年)《五禮通考跋》亦言:“吾師味經師長教師因徐氏《讀禮通考》之例而遍考五禮之沿革,博取精研,凡用功三十八年而書乃成。”[9]
《通典》
唐代杜佑的《通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系統記載歷代軌制的通史,分八門: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10]。共200卷,禮門占了100卷,按禮典目錄(1卷)、吉禮(14卷)、嘉禮(18卷)、賓禮(2卷)、軍禮(3卷)、兇禮(27卷)、開元禮纂類(35卷),分述禮制因革。須加留心的是,《開元禮》原吉、賓、軍、嘉、兇的“五禮”順序被《通典》的纂類改作吉、嘉、賓、軍、兇,并成為“五禮”的普通性順序。《五禮通考》以《周禮·大批伯》所言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五禮”為綱,卻不采用它的排序,而以《通典》為據。
《文獻通考》
成書在元初的《文獻通考》以《通典》作藍本,不過對于中國典章軌制的懂得更寬泛,其分類與《通典》也有所區別。[11]作者馬端臨對中國典制的總體掌握及分類對后世具有很年夜的影響及參考意義。現代碩儒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中批評《五禮通考》分類“未當”時,就舉《文獻通考》作為對比的對象[12]。《五禮通考·凡例》曾對《通典》、陳祥道《禮書》、《儀禮經傳包養價格ptt通解》和《文獻通考》進行比較,由此可見,當時秦蕙田在謀劃商討《五禮通考》的篇章內容時,對《文獻通考》的門類結構必定細加考核,以資鏡鑒。曾國藩曾將《五禮通考》與“三通”(即《通典》《文獻通考》及鄭樵《通志》)并論,以為可成“四通”,由此招來章太炎的微詞[13]。
在書寫的體例格局上,《文獻通考》對《五禮通考》也留下烙印。《文獻通考·自序》曾解釋:引古經史為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是為“文獻通考”[14]。“文”頂格書寫,“獻”降一字書寫,以示區別。作者的按語則再低一字書寫。《五禮通考》則將征引之資料分為三類:頂格書寫,降一字書寫,少數降二字書寫。類似分頂格與降格書寫的情勢,《儀禮經傳通解》《讀禮通考》曾予采用“今所定規,傳記之附注者低一字,它書低二字。”[15]
很巧的是,以上四部書及《五禮通考》,書名中都有一個“通”字。這大要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應出,唐宋以降,在中國知識界,慢慢構成了一種講求“會通”的學術取向;并且又漸漸延展到禮學領域,特別是到了清朝。天然,各有各的“會通”特點。這里集中討論《五禮通考》,先擇其三點論述。

【圖為馬端臨《文獻通考》梅墅石渠閣版書影】
(一)融匯“三禮”,《儀禮》《周禮》并重
對《周禮》《儀禮》《禮記》分歧的評價及彼此關系的分歧懂得,漢代已成訟案。至宋代,一方面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16];另一方面從歐陽修、蘇軾、蘇轍到胡宏、包恢[17],不斷質疑《周禮》。這般等等,使舊話題增加了新命意,包養心得同時也給后起的禮學家設下繞不開的“路障”,必須面對并予以回應。朱熹就有興趣構建新的禮學體系,并試圖會通“三禮”學。《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經,附以《禮記》和其他諸書[18],同時朱熹又愛崇《周禮》。秦蕙田站在會通“三禮”的立場上,更極力調和歷史上有關《周禮》《儀禮》孰為本、末的議論,以此表達同樣推尊《周禮》和《儀禮》。
《五禮通考》卷首第一《禮經作述源流上》開篇即從周公制禮說起。起首引王通的話:“吾視千載而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繼而引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言:“《周》、《儀》二禮并周公所制”;“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始終,分為二部,并是周公攝政承平之書”。針對陸德明說“‘三禮’次序遞次,《周》為本,《儀》為末”,而賈公彥則主張“《周禮》為末,《儀禮》為本”,《五禮通考》以按語情勢加以調和、折衷、互補。以下是《五禮通考》的第一則按語,署的名是該書編撰的主要參與人方觀承[19]:
觀承案:陸氏謂《周》為本、《儀》為末者,《周禮》乃禮之綱要,《儀禮》乃禮之節目也。賈氏又謂《周禮》為末、《儀禮》為本者,《周禮》乃經世宰物之宜,包養app《儀禮》乃敦行實踐之事也。
所以有學者指出:《五禮通考》“吞吐百氏,剪裁眾說。蓋舉二十二史,悉貫以《周禮》《儀禮》為之統率”[20]。
(二包養dcard)兼采經傳、史志、紀傳、儀制、會典、實錄、類書等各類載籍,搭建龐年夜的禮學知識系統
《五禮通考》分歧于《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經,也有別于《讀禮通考》的內容僅限于喪禮,而是按五禮及分類條目,收羅自先秦至明代的各種資料,觸及經傳、史志、紀傳、儀制、會典、實錄、類書等各類載籍,“悉以類相附,詳歷代之因革,存古今之同然”[21]。秦蕙田顯然遵從了徐乾學廣泛搜羅禮學資料的做法,并推而廣之。《士喪讀禮通考援用書目》(載《讀禮通考》卷首)揭舉了經、史、子、集631種著作,而《五禮通考》的援用范圍更廣。以《五禮通考》卷四十五“社稷(城隍附)”為例,此卷敘述明代社稷和歷代祭城隍的禮制,其引資料的出處包含:《明史》(包含《太祖本紀》《世宗本紀》《禮志》《樂志》《張籌傳》等)、《春明夢余錄》、《明集禮》、《續文獻通考》、《明會典》、《太祖實甜心寶貝包養網錄》、《成祖實錄》、《仁宗實錄》、《宣宗實錄》、《孝宗實錄》、《世宗實錄》、《太常紀》、《年夜政記》[22]、《承平府志》、《北齊書》、《冊府元龜》、《宋史》、《元史》、《圖書編》、《日下舊聞(考)》和《圖書集成·城隍祀典部·藝文》、張九齡《祭洪州城隍神祈晴文》、杜牧《祭城隍神祈雨文》、李商隱《祭桂州城隍神祝文》、後人《為安平公兗州祭城隍文》、後人《為懷州李使君祭城隍文》等。恰是因其引述文獻之宏富,搭建的禮學知包養網推薦識系統之龐年夜,才獲得“絕無僅有”之稱。
(三)買通禮經(經典)和儀制(操縱)包養女人的界隔,創擬“五禮”新體系
《五禮通考》卷首有兩篇相對獨立的文字,一是“禮經作述源流”(分上、下),一是“禮制因革”(分上、下)[23]。“禮經作述源流”分“禮經作述年夜指”“經禮威儀之別”“禮經傳述源流”三部門。“禮經作述年夜指”究詰《周禮》《儀禮》《禮記》的禮書性質及其關系,有兩則按語,第一則前文已揭引(即“觀承案”),第二則是針對後人所謂“武帝嘗作《十包養網站論》《七難》,以排之(本文作者按:指《周禮》)不立學官,而何休詆為戰國陰謀”一說而發,文字不長,如下:
宗元案:《十論》、《七難》乃林碩作,非武帝也,此誤。
宗元,即宋宗元,字愨庭,元和人,與秦蕙田交游頗深,參與編撰《五禮通考》。“經禮威儀之別”重要討論若何懂得“經禮三百”與“曲禮三千”。編者未出按語,所有的靠引述[24]。
“禮經傳述源流”以野史的藝文志、經籍志為重要依據,參以《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和其他史傳資料,介紹歷代禮經的傳述。這部門內容有點類似于目錄學的記敘,敘說的順序是:《周禮》《儀禮》《禮記》,最后是“三禮”和雜禮。有“蕙田案”按語一條。
“禮制因革”概述明代(含明代)以前禮制的制作和演變,所引資料從《尚書》《周禮》《禮記》《論語》《左傳》《國語》而下,以野史的“禮志”(“禮書”“禮儀志”“禮樂志”)為主體,結合《唐會要》《唐六典》《玉海》《通典》《續文獻通考》《歷代名臣奏議》《元典章》《年夜政記》及其他史志、史傳、官簿,兼及《朱子家禮》和邱濬的《年夜學衍義補》等,有四則按語所有的是“蕙田案”,且所有的在“禮制因革·上”(唐以前部門)。茲引此中一例,以見一斑:“蕙田案:禮莫盛于成周,漢興三百余年,西京未遑制作。雖有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諸人,班志所載,僅存議論。惜哉。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三代’之治,所以不復見于后世也。”。其獨到的視野和敘述,勾畫出一部簡明的中國禮制發展史,具有創新意義。
還須垂注的是,“禮經作述源流”和“禮制因革”猶如全書的兩篇總綱,“五禮”通考是綱舉目張之產物。唯此“綱”由兩年夜主線(禮經與禮制,或儒學典籍與官府儀制)交錯、融會而成。從而《五禮通考》創擬了一個具有新意味的“五禮”體系。
二
《五禮通考》篇幅之年夜,不單在《四庫全書》的禮類並且在整個經部著作中,都排名第一。能與之頡頏者,只要經部之外的一些巨構,如《宋史》《明史》《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六藝之一錄》等。前文論及的《儀禮經傳通解》(原三十七卷,缺卷十五;此中第二十四卷至第三十七卷因非朱熹親定,仍題名《儀禮集傳集注》)及黃榦、楊復《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卷),在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合為2冊,此中《儀禮經傳通解》為604頁,《儀禮經傳通解續》是1044頁。即以這等規模,《儀禮經傳通解》的撰作,已著實讓朱老漢子一輩子都費心不完[25]。那么,皇皇《五禮通考》畢竟是若何撰作完成的,就不克不及不引發人的興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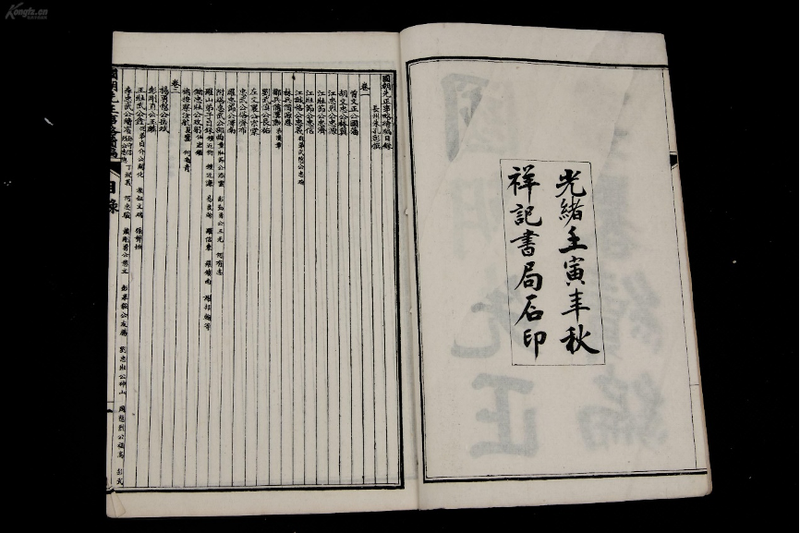
【圖為《國朝先閒事略》書影】
秦蕙田位居高官,且勤政實干[26],這使他一定喪台灣包養掉大批可用于治學的時間,分歧于職業學問家。但另一方面,因為位高權重,加之本身的出生、眼界、學養等而構成的人格魅力,卻讓他又有條件吸引和羅致人才,調動各種資源,借助眾手協力修書,這顯然是《五禮通考》得以完帙的很主要緣由。秦蕙田于乾隆元年(1736年)考取進士,后宦途順遂。至十年(1745年),已遷為禮部右侍郎。后調任刑部侍郎,又擔當經筵講官。其后,更升任工部尚書、刑部尚書,并加太子太保,還兩次擔任會試正考官。是以,秦尚書身邊能夠團聚一批有才學的人士,共襄盛舉。自秦蕙田因父喪還鄉丁憂,杜門讀禮,受《讀禮通考》啟發而撰作《五禮通考》,即有早年老友吳遵彝配合竭力。其后秦蕙田回京,仍得方觀承、盧見曾、宋宗元諸人的一起配合幫助。《五禮通考》初稿成型后,又邀請了一大量學者參與校訂。
圣環本“《五禮通考》卷首第一”題名之下,署有: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國子監司業金匱吳鼎、按察使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該本《五禮通考總目上》和《五禮通考總面前目今》題名之下,還署有: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監理樂部年夜臣協理國子監算學前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太子太保總督直隸監管河流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27]。這直接記錄了一部門撰作實況。
又,徐世昌《清儒學案》卷六十七載,當時參加《五禮通考》校訂任務的有:“金匱吳氏鼎,德州盧氏見曾,元和宋氏宗元,嘉定錢氏年夜昕,王氏鳴盛,休寧戴氏震,仁和沈氏廷芳,吳江顧氏我鈞。其吉禮屬吳氏、盧氏、顧氏。嘉禮屬錢氏者,昏、饗、燕、鄉飲酒、學諸禮,及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兩年夜類;屬王氏者,射、巡狩;屬戴氏者,觀象授時一年夜類包養平台。賓禮全屬錢氏。軍禮全屬王氏。兇禮屬錢氏、沈氏、吳氏、盧氏。惟宋氏所參校者十及八、九,統校全書則屬諸山陽吳氏玉搢焉。青浦王氏昶亦預參校。”《清儒學案·味經學案》。該段文字之后,緊接著又言:“而卷中未分注名氏。”此中承擔軍禮和嘉禮的射、巡狩部門校訂的王鳴盛(1722—1797年),乃清代三年夜考史名著《十七史商議》的作者。承擔賓禮和部門嘉禮、兇禮的錢年夜昕(1728—1804年),其所著《廿二史考異》是另一部考史名著。所言戴氏,為戴震(1723—1777年)。僅此三位巨頭,已足見這個修書班子底蘊之深摯。雖然王、錢、戴當時尚屬年輕,然也唯因這般,才有能夠參加到別人的著作活動中往。
從錢年夜昕上面的話中,可以確定秦蕙田屬于學者型的權要,為學、向學之心終生不渝,同時獎掖后進,具有凸起的人格魅力:
公(本文作者按:秦蕙田)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送上以敬,剛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則杜門謝賓客著書,不異為諸生時。后進有通經嗜古者,獎借不往口,蓋本性然也。公幼而穎悟,及長,從給諫公于京邸,何紀瞻、王若林、徐壇長諸師長教師,咸折輩行與之交。中歲居里門,與蔡宸錫、吳年夜年、尊彝、龔繩中為讀經之會。嘗慨禮經名物軌制,諸儒詮解互異,鮮能會通其說,故于郊社、宗廟、包養網VIP宮室、衣服之類,尤究心焉。上御極之初,江陰楊訂婚公領國子監事,薦公篤志經術,可佐教成均。既而值內廷,課皇子講讀,益以經術為后學宗。……公夙精三禮之學,及佐秩宗,考古今禮制因革。[28]
王鳴盛的記錄更可證明秦蕙田不僅組織眾人修撰《五禮通考》,並且更實質性田主持其事,并親自參加討論和寫作:
公每豎一義,必檢數書為佐證。復與同道往復討論,然后筆之。故其辨析異同,鋪陳本末,文繁理富,繩貫絲聯,信可謂博極群書者矣![29]
方觀承的《包養網心得五禮通考序》,則從另一側面供給了清楚一起配合者之間關系的管道:
昔在京師時,伯父看溪師長教師(本文作者按:方苞)奉詔纂修《三禮》,余數從講問。……因以所著《喪禮或問》授余。既而閱昆山徐氏《讀禮通考》,乃知圣人立中制節。《或問》實揭其精微若載。《或問》于喪禮補吊、荒、禬、恤之制,則兇禮已全。準是而師朱子輯禮本意,博采經傳子史,區為吉、嘉、賓、軍四類,而匯成《五禮全書》。庶幾經世年夜典,可以信今而垂后也。吾友味經師長教師以博達之材,粹于禮經,官秩宗,日侍內廷,值圣皇帝修明禮樂,乃益好學沉思,研綜墳典。上自六經,下迄元明,凡郊廟、禋祀、朝覲、會同、師田、行役、射鄉、食饗、冠婚、學校,各以類附。于是五禮條分縷析,皆可依類以求其義。師長教師向與伯父論禮,因屬余參訂,爰考歷代之沿革,諸儒之異同,有所見輒附于其間。非謂能折衷禮制也。……是書體年夜物博,師長教師積數十年搜討參伍,乃能較若畫一。[30]
由此,我們就可消除圍繞《五禮通考》成書問題上的一些不實之辭。如梁啟超說:“(徐乾學的《讀禮通考》,所有的由季野捉刀)秦蕙田的《五禮通考》,生怕多半也是偷季包養金額野的。”[31]這既缺少依據,也有悖道理——試想,這般浩蕩的修書工程,豈是憑萬斯同(字季野,1638—1702年)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須知,萬斯統一生不僅“把五百卷的《明史稿》著成”,同時還有大批的其他各種著作[32]。至于徐乾學《讀禮通考》的成書,可參見《四庫全書總目·讀禮通考撮要》:“蓋乾學傳是樓躲書,甲于當代。而一時通經學古之士,如閻若璩等,亦多集其門,合眾力以為之。故博而有要,獨過諸儒。”(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6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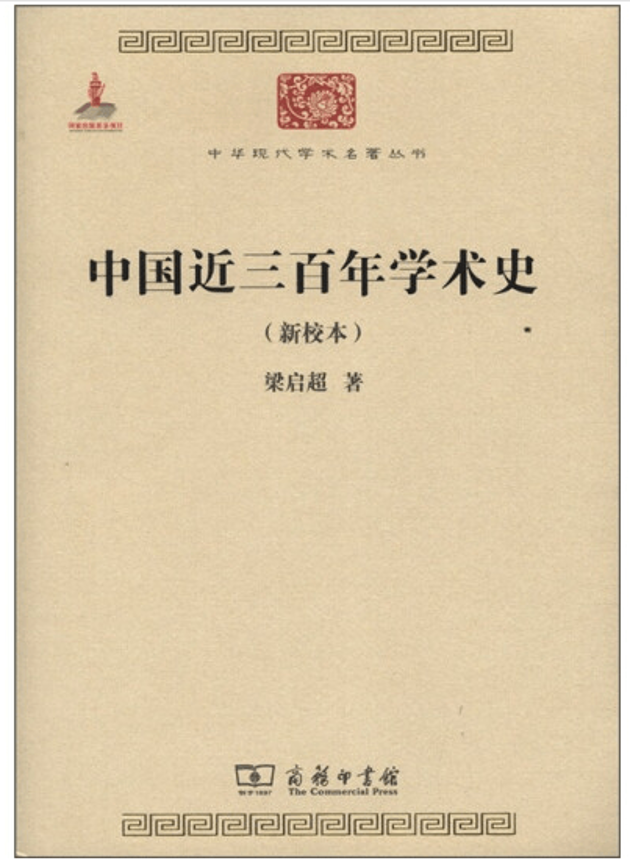
【圖為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影】
這就觸及中國現代一種撰作活動的類型(宋代以后開始多見,此中又有各種分歧的亞類型)。集體參加或借助別人之力是其基礎特點,但號召力和凝集力(也可以說是驅動力)卻有所分歧。像朱熹撰作《儀禮經傳通解》,最後曾想尋求朝廷的支撐[33],但最后還是憑借其導師和精力領袖的成分來加以組織和動員。秦蕙田撰作《五禮通考》(包含此前的徐乾學、稍后的阮元等)則稍微復雜一些。我們應該正視這種“撰作活動的類型”,這對懂得《五禮通考》的價值和特點是有幫助的。當然探討這種類型已越出本文的宗旨,所以點到為止,容日后再作展開。
秦蕙田的家庭佈景和個人閱歷,為他以會通之方式研討禮學,撰作《五禮通考》,供給了圖書資料方面的必須條件。秦蕙田生于江南世家,宋代秦觀第二十六世孫,祖父、父親都享有文名,通經學、擅詩詞。蔣汾功《五禮通考序》言:
予與秦氏世好……素知其家多躲書,凡禮經疏義外間絕少刊本而庋貯緘題者,數十笥。宗伯以絕人之姿,盡發而讀之,早歲即洞其條理,綜核纂注,匯為一編。[34]
這里所言“匯為一編”,當指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所講少時在“讀經之會”基礎上,“考辨如是者,十有余年,而裒然漸有成秩矣”。比及秦蕙田“供奉內廷,以見聞所及,時加厘正。……服闋后再任容臺,遍覽典章,日以增廣”[35]。長期在京城上層活動,使其有條件接近各種資料,拓寬視野,為學術研討創造了方便。
《五禮通考》絕少觸及本朝,并從體例上框定“通考”的上限只及明朝。《五禮通考·凡例》最后說明:“洪惟我朝,圣圣相承,軌包養網比較制修明,日新富有。至于科條所頒,敬切訓行,精深莫贊。蕙田叨佐秩宗,疏陋是懼,復理專門故業,略識源流,抑亦退食寢興無忘匪懈云耳。”這里對于《五禮通考》敘述考辨為何“迄于前明”,并不詳解,語意晦澀。這一做法似乎有需要聯系其家庭佈景加以考量。雍正時,蕙田之本生父秦道然因皇室內部的牴觸而受牽連,下獄一關就是九年。至秦蕙田進士落第,“授編修,南書房行走”,遂上疏向乾隆天子“乞恩”:盼望父親在“八十病篤之年,得以終老牖下。臣愿奪職效奔忙以贖父罪”。乾隆天子乃赦免其父[36]。家庭中這般極重繁重的創痛,必定會對秦蕙田的為人處世包含治學的內容與情勢產生影響。史稱秦蕙田“治事勤敬”[37]“恪勤素著”[38],生怕便是此中的一個面相。而盡量回避對本朝的評論,則能夠成為另一種保存戰略。
秦蕙田自稱“性拙鈍,少讀書不敢為詞章淹貫之學”,從小即留心于經學,“塾師授之經,循行數墨,恐恐然若掉也”[39]。這當然可以從一個角度解釋其對學問的選擇,但是同樣不成疏忽的是,秦蕙田后來長期從事實際政務任務的經歷,必定會強化其對“踐履”的重視與強調,主張學乃至用。這也就為其盡數十年之力不倦于《五禮通考》的撰作,供給了耐久的動力。進而,也會不斷地促使他融通各種學說和知識,努力于禮學的會通。秦蕙田和《五禮通考》能獲得同樣身為官宦的曾國藩之懂得和贊慕,似有內在關聯。
不成疏忽的還有,秦蕙田的誕生地、成長地無錫(雍正時新辟為金匱縣)的地區文明,對《五禮通考》撰作的影響。明清時期,工商文明已在江南一些地區蔚然興起(無錫具有代表性),其講求實際和實用的價值取包養金額向,與經世致用的學風互為推助。還有,徐乾學乃昆隱士,其地與無錫甚近。《五禮通考》寫作班子中,錢年包養甜心夜昕、王鳴盛都是嘉定人,嘉定與無錫同在蘇南。而戴震、方觀承也毗鄰江南文明圈。這一切,確定有地區文明上的關聯存在。
三
《朱子語類》卷八十四載:“禮樂廢壞兩千余年,若以年夜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后來須有一個年夜年夜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40]朱熹的話,或許能代表宋代以后一些文人儒士的思惟與情志,并且,這種情志與思惟投射到了禮學研討之中。禮學成為依靠社會幻想、寄寓治世良方的學問。
乾隆元年(1736年)詔開“三禮館”,乾隆十三年(1748年)修成《欽定周官義疏》《欽定儀禮義疏》《欽定禮記義疏》。繼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又頒定《年夜清通禮》。由此新一波的禮學研討海潮,執政野高低蔚然興起。秦蕙田置身其間,以《五禮通考》的撰作貢獻于眾人。
晚近包養意思,學人有《以禮代表——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惟之轉變》和《清初三禮學》[41]等結果問世,對于17—18世紀禮學的啟承轉變作了深刻的梳理、闡說,多有發明。但秦蕙田和《五禮通考》在此進程中的位置和感化,卻未獲得正面的研討,從而留下主要的缺環。劉廣京師長教師慧眼洞見,1999年在給張壽安《以禮代表》年夜陸版作序時,結尾處就特地提到,秦蕙田完成《五禮通考》,“時已屆戴震(1723—1777)著作之年,與張師長教師本書所論時代已可銜接。世運推移,而學則垂久。后世論禮學及情欲之學,皆有所本矣”。
當年,王鳴盛《五禮通考序》對秦蕙田治學取向及其特點有極精要的總結:“秦公味經師長教師之治經也,研討義理而輔以考索之學,蓋守朱子之家法也。”針對別人誤以為《五禮通考》不過是“補續徐氏”,秦蕙田曾特地向王鳴盛聲名:“此蓋將以繼朱子之志耳,豈徒欲作徐氏之元勳哉。”[42]其禮學的抱負一言以明。
假設用一個字來歸納綜合《五禮通考》所代表的秦蕙田的禮學的話,大要就是“通”。除了本文第一部門論說的三個方面,“通”還表現在:漢學、宋學兼采,義理與考索之學相結合,以禮學經世為指歸,廣綜博攬。
反應在“五禮”的內容和范圍上,其“通”的特點也是超出後人的。如“以樂律附于吉禮宗廟軌制之后。以地理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水、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并載進嘉禮”。此舉后惹起四庫館臣的議論,以為:“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難免有炫博之意。”好在秦蕙田當初就已說明:“《通考》將田賦、選舉、學校、職官、象緯、封建、輿地、王禮各為一門,不進五禮。而朱子《經傳通解》俱編進王朝禮,最為該恰。今祖述《通解》,稍變體例,附于嘉禮之內。”[43]由此,四庫館臣緊接著後面那句話,又將語氣緩轉過來,說:“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之用,精粗條貫,所賅本博。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于學禮載鐘律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書數篇而未成。則蕙田之以類纂附,尚不為無據。”[44]恰是秦蕙田這種融通的視野和伎倆贏得了曾國藩的高度贊譽:“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罷了。……《五禮通考》,自地理、地輿、軍政、官制,都萃此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45]該文接著又說:“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為一編,傅于秦書之次,非徒廣己于不成畔岸之域。先圣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故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槧之不成以茍,未及事事,而齒發固已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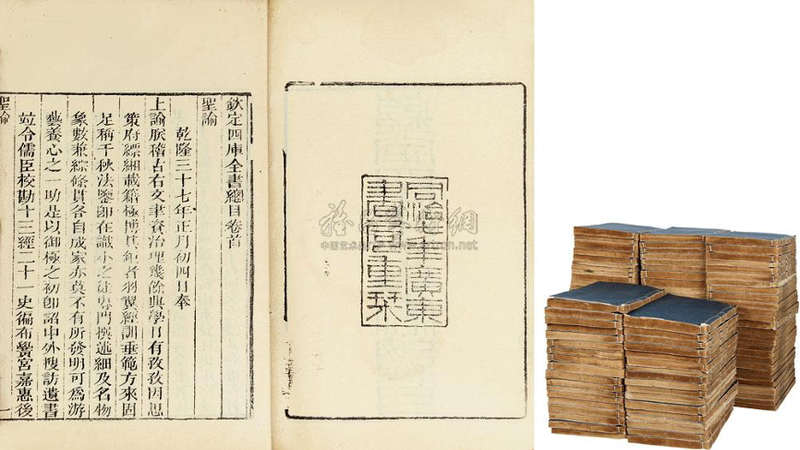
【圖為《四庫全書總目》書影】
至此,本文用“通禮”來歸納綜合《五禮通考》的著作形態。這既是一種新的禮書編撰情勢,也包括著禮學的一種新形態。秦蕙田在禮學史上的最年夜業績,就是在後人的基礎上發展了這一著作形態。
但是說到“新”,天然是有局限的。最關鍵者,莫過于歷史觀。茲援用兩段話,來反應秦蕙田的歷史觀——
(1)乾隆《御制重刻文獻通考序》:“會通古今包養犯法嗎,該洽載籍,薈萃源流,綜統同異,莫善于《通考》之書……夫帝王之治全國也,有不敝之道,無不敝之法,包養留言板綱常倫理萬事相因者也,忠敬質文隨時損益者也,法久則必變,所以通之者必包養sd監于前代,以為之調和。”[46]
(2)《五禮通考》卷首第一《禮經作述源流上》:“朱子曰……《周禮》乃周家盛時圣賢制作之書。《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年夜心中流出。《周官》遍布緊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
《五禮通考》既是這種歷史觀的產物,也成為表達和維護這一歷史觀的東西。
受這種歷史觀指導所進行的以考辨、折衷為重要手腕的學術任務,其意義畢竟幾何,天然就令后人生疑。“新史學”倡言人梁啟超,就強烈地質疑此前的禮學研討:“這門學問究竟可否成立,我們不克不及不最基礎懷疑。”[47]
現在看來,“懷疑”并不難,難的是若何由懷疑而邁向更高的認識水包養網比較準。本文是向著這個目標而進行的一項基礎性研討,盼望借此清楚現代禮學在步進終結前最后一段歷程的一些具體情況。
注釋:
[1]這8冊的頁數分別是:1163頁,1101頁,989頁,1084頁,901頁,548頁,734頁,797頁。此中第134冊為合集,還有340頁,包養價格ptt支出了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等5種著作。關于字數,是按原刊本每半頁8行、每行21字計算,影印本縮印為四合一十六開本。鑒于此中有不少以夾注情勢小字雙行謄抄,所以縮印本以均勻值每頁670字計算,絕不高估,總字數490萬字實屬守舊預算。
[2]顧棟高:《五禮通考原序》,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五禮通考》卷首。如不特別揭舉,本文即依據此本。
[3]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八《五禮通考跋》,上包養網ppt海古籍出書社《續修四庫全書》本,冊1432,第626頁。
[4]《圣哲畫像記》,《曾國藩選集·詩文》,岳麓書社,1986年,第247—252頁。
[5]王煒平易近:《秦蕙田與〈五禮通考〉》,《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
[6]林存陽:《秦蕙田與〈五禮通考〉》,《北京聯合年夜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7]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五禮通考》卷首。
[8]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五禮通考》卷首。
[9]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八《五禮通考跋》,上海古籍出書社《續修四庫全書》本,冊1432,第626頁。
[10]茲沿用《四庫全書總目·通典撮要》的說法,見中華書局影印本,第693頁。《通典》將“兵”“刑”析而為二。
[11]《文獻通考》分二十四考(門),此中“十九門皆因《通典》而離析之……五門則《通典》所未及也”《四庫全書總目·通典撮要》。
[12]章太炎:《國學講演錄》,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1995年,第154—156頁。
[13]章太炎:《國學講演錄》,第154—156頁。
[14]此話亦為《四庫全書總目·文獻通考撮要》所徵引。
[15][15]見文集卷六十三《答余正甫》書二。陳俊平易近校編《朱子文集》,改“附注者”為“附經者”,有校勘記云:“‘經’字原誤作‘注’,依浙監本改。”“德富古籍叢刊”本,臺灣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指定版本,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另,《讀禮通考》有一類不標明“乾學案”的很短的按語,低一格書寫。如卷十四:“《家禮》、今律文并同,《孝慈錄》、《會典》俱無,《會典》圖內有之。”“《政和禮》、《家禮》、《孝慈錄》、《會典》、今律文并同,唯《書儀》無。”。《五禮通考》及《讀禮通考》還因襲了以按語情勢來陳述作者的觀點,書寫格局上為降四字,顯得較為奪目。
[16]語見《四庫全書總目·儀禮經傳通解撮要》,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79頁。
[17]包恢,南宋嘉定十三年進士,《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支出其《敝帚稿略》。總目撮要言:“恢生平最疑《周禮》,以為非圣哲之書,遂著書剖其非,號曰《周禮六官辨》。”
[18]被《四庫全書總目·儀禮經傳通解撮要》徵引的朱熹早年的《乞修三禮札子》,就明白表達了這個意見:“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禮者,皆以附于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文見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四川教導出書社,1996年,第569頁。朱熹甜心花園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所以認為“《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見文集卷五十《答潘恭叔》書四。陳俊平易近校編《朱子文集》標點為“《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
[包養行情19]方觀承,字宜田,有名學者,桐城人,方苞之侄,圣環本《五禮通考》卷首有其《五禮通考序》。文淵閣四庫本卷首有蔣汾功序(作于乾隆十八年)、顧棟高序(作于乾隆十七年)和秦蕙田自序,未支出方觀承序。
[20]盧見曾:《五禮通考序》,《雅雨堂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書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23冊,第454頁。盧見曾,字抱孫,德州人,與秦蕙田交游頗深。
[21]顧棟高:《五禮通考原序》,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五禮通考》卷首。如不特別揭舉,本文即依據此本。
[22]據《明史·藝文志》:《太常紀》,二十二卷,呂鳴珂撰;《年夜政記》,三十六卷,雷禮撰。
[23]《五禮通考》卷首三題名“禮制因革上”,《五禮通考》卷首四題名“禮制因革下”,但在“目錄”中,“禮制因革”卻被易名為“歷代禮制沿革”。“禮經作述源流”“禮制因革”(“歷代禮制沿革”)凡4卷,加註釋262卷,所以《五禮通考》總計266卷。
[24]所援用的第一則資料是:孔氏穎達曰:《周禮》見于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年齡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禮經作述年夜指”和“經禮威儀之別”兩部門共徵引了歷代20多位有名學者的觀點此中有:隋朝王通,唐代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韓愈,宋代程顥、程頤、周谞、呂年夜臨、晁公包養意思武、楊時、葉夢得、朱熹、王應麟、馬廷鸞,元代熊朋來、敖繼公,明代湛若水、童承敘、王志長、郝敬,包養甜心網清代徐乾學、萬斯年夜、姜兆錫。
[25]束景南《朱子年夜傳》曾描寫在朱熹率領下,若何集體編寫《儀禮經傳通解》,并抽像地說,朱熹一度組織了三套寫作班子分工一起配合、齊頭并進。見該書第1012頁(福建教導出書社,1992年)。
[26]有關秦蕙田生平,可參見《清史稿》卷三〇四《秦蕙田傳》;李元度輯:《國朝先閒事略》卷十七《秦文恭公務略》;《清史列傳》卷二十《秦蕙田》等。
[27]文淵閣四庫本沒有類似的記錄。另,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卷六十七《味經學案》載:“(《五禮通考》)書成,方恪敏觀承見而好之,同為商訂,故并列名焉。”(臺灣中華年夜典編印會等,1967年)對此,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亦有交接。
[28]錢年夜昕:《文恭公墓志銘》,《潛研堂文集》卷四二,上海古籍出書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39冊,第158頁。
[29][29]王鳴盛:《五禮通考序》,《西莊始存稿》卷二四,上海古籍出書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34冊,第318頁。
[30]方觀承:《五禮通考序》,圣環本《五禮通考》卷首。
[31]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包養情婦史》,見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年夜學出書社,1985年,第194頁。
[32]王鳴盛:《五禮通考序》,《西莊始存稿》卷二四。
[33]參見朱熹:《乞修三禮札子》,《朱熹集》,四川教導出書社,1996年,第569頁。
[34]蔣汾功:《五禮通考序》,載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五禮通考》卷首。
[35]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
[36][36]《清史稿》卷三〇四《秦蕙田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0503—10504頁。
[37]李元度輯:《國朝先閒事略》卷十七《秦文恭公務略》,上海古籍出書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538冊,第387—388頁。
[38]《清史列傳》卷二十《秦蕙田》引乾隆天子上諭,中華書局王鐘翰點校本,第1480頁。
[39]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
[40]《朱子語類·禮一·論考禮綱領》,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177頁。
[41][41]張壽安:《以禮代表——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惟之轉變》,河北教導出書社,2001年;張氏還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惟活氣——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發行(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林存陽:《清初三禮學》,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02年。
[42]王鳴盛:《五禮通考序》,《西莊始存稿》卷二四,上海古籍出書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34冊,第318頁。
[43][43]《五禮通考·凡例》,《五禮通考》卷首。
[44]《四庫全書總目·五禮通考撮要》,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79頁。
[45]《孫芝房侍講芻論序》,《曾國藩選集·詩文》,第256頁。
[46]中華書局影印本《文獻通考》卷首,第1—2頁。此雖非出自秦蕙田之手,亦未為其所引,卻與其禮學思惟極相合。
[47]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312頁。
責任編輯:近復